關於黃明鍾-創作自述
一、生命故事
50多歲的我,在八七水災的那年罹患了小兒麻痺症。小時候住在三義僻遠山區的小農村,與外界的交通相當不便,一般人要步行二、三十分鐘才能到街上,對我而言,這段路是頗為吃力的,需要一個小時,有時還需要體形嬌小的母親(用扁擔一邊挑著菜或石頭,一邊就是我了),或與我年齡不差上下的兄弟們背我下山;當時生活清苦,佃農的父親,要養一家十口,大哥、大姊因家境清寒,國小一畢業就外出打工,排行第三的我,在當時衛生所的主任協助下,順利完成國中學業。之後,父親對我這個殘障兒子未來謀生的能力做了一番的思考,決定安排我到堂舅家去學木雕,當時木雕界正是高峰期,父親原以為我將是家中最有成就的兒子,但我後來竟選擇了木雕創作,這點他一直不能諒解我。選擇創作這條不歸路的同時,一心想從創作中尋求生命成長,過程中雖有豐富的心靈滋潤,但不穩定的收入,省吃儉用,曾經從事半年以上粗重的鐵工,至終以貸款為生。 艱辛的生活,不敢有任何成家的念頭,雖然已到適婚年齡,親友不斷的催促,也只能交交女朋友,不敢有結婚的打算。然而,老天爺疼惜我這個老實人,在90年年底,我的生命中出現了一位勇者~那就是我的老婆(我們是在一場殘障朋友的未婚聯誼活動裏,速配成功的一對)。 明知道我的經濟狀況,也知道我的工作性質,仍排除眾議,成為我終身的伴侶。寫到這裏,也許有人以為我是挖到了金礦,我的老婆應該很有錢,若是您是這麼想,您就錯了。她跟我一樣,我們都沒有多少的收入,但我們有一個心志,「夫妻同心,泥土變黃金」,現在的苦不是真苦,只要我們願意一起努力,我們相信是可以突破許多困難的。的確,近六年的婚姻生活,物質生活不是那麼的充裕,精神生活卻是讓我們心靈更相契,再加上有了一個愛情的結晶,生命更是豐盛美滿,有如倒吃甘蔗一般。
二、創作生涯
我,黃明鍾,生於1958年,家住苗栗三義,1973年國中畢業,第二年便至苗栗市張耀桂先生開設的「藝宗軒」學雕刻,扎實地接受了三年四個月的木扁、廟寺、家具裝飾的傳統雕刻技術。後輾轉回三義劉明源先生的工作室,學習立體雕刻五年,雕刻花鳥、屏風,屬裝飾性的工藝品。1987年嘗試創作,1990年排除眾議,毅然決然地走上創作之路。 六年後(1996、1997)幸蒙二次國家文化基金會的創作補助。十多年來的創作生涯裡,在不少的反對聲浪中,歷經了經濟的窘困、生活的艱辛,並忍受著孤寂,仍努力的創作,因為這是一份自詡值得終身投入的事業,甚至可說是生命的出口。創作之於我,亦可說是一種的藝術治療,每每投入創作中時,那種喜悅是難以形容的。 由於作品漸為大眾所肯定,屢獲獎項,並受邀擔任木雕研習營的講師,投入培育木雕藝術人才的行列裡。未來的生涯裡,仍是以木雕創作為主體,更期望的是,作品能到國外展出。在前年巧遇一位匈牙利的木雕創作者-艾立克,邀我今年七月參加匈牙利/塔塔班牙的國際創作營,今正為旅費傷腦筋呢!
三、創作歷程
有人問我:「走上藝術創作的這條路,後悔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雖然,一路走來十分艱辛,收入來源不穩定,即便是孤家寡人一個、一口飽全家飽的狀況,經濟壓力仍是不小;但是,在創作過程中,我得以真誠、赤裸地面對內在的自我,透過一次次的自我對話,紓解了內心的壓抑與鬱悶,這種近似自我治療的行為,免除了我幾近精神崩潰的危險。我常想,如果沒有創作的行為,或許,我早已進入杜鵑窩了。 從傳統學徒轉變為從事創作,其原因十分單純,由於受傷的緣故,我的體力與力道再也無法負荷以前的工作,如要繼續刻下去,勢必得換種方式來走。早年從事創作時,腦袋裡懵懵懂懂的,也搞不清藝術為何物?沒有太多的知識和包袱,純粹是自我哀怨和呢喃,藉由一刀一刻的過程,平緩了心中長久來的哀嘆和怨恨。封閉在個人的象牙塔了,獨自啃食著自小到大,在環境中所遇到的歧視和屈辱;創作之初,我雖無意吶喊種種不平,但是,憂愁之容總是不經意地緩緩流現。 不可否認地,學院的知識和判準,對我這個門外漢而言,確實具有幾分魅力;在和學院人士的接觸裡,我也學著探索材質、結構、形式與內容的問題,甚至,思索著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的文化差異和表現特色。然而,這一切卻是初踏創作之路時的我,無心關照的事,我很慶幸自己不再囿限於過往個人的不快經驗,得以打開心胸面對外在的世界。 創作歷程的轉變和作品形式的變化在所難免,但是,「回到原點、回到最初創作時的純粹、回到最直觀的自我表現,保有並呈現出內在自我不變的本質」,則是我創作上仍須努力的目標。
四、朋友眼中的我
[彭賢祥] 我永遠記得相識之初,在台北某家頗具盛名的畫廊,他固有鄉下人的靦腆與一拐一拐的跛行總讓我覺得他與畫廊空間格格不入。後來,知道了他往後幾年的困頓,才瞭解這幾年來他創作的艱辛。也許「文窮而後工」,這幾年來,黃明鍾不斷地克服物質的匱乏與肢體的殘障創作不懈。他的作品早已脫離傳統木雕的匠氣,而突顯出個人獨特悲憤、鬱結的風格。這個過程中,雖然,有一個時期受到學院形式主義的影響,轉向幾何、抽象的造形,但他終究轉回自己的生命原型,並試圖藉創作昇華生命的掙扎與無奈,轉化為澄靜與恬淡。 對於黃明鍾的創作,真正吸引我的不在於過程的艱辛曲折,而在於他作品獨特的個人語言。首先,從形式來講,黃明鍾作品的造形常常帶著一種傾斜、不安定的平衡感,看似矛盾的結合,卻是十分耐人尋味,這種獨特的平衡不是藝術家刻意追求造形的「奇險」,而是藝術家身體的意象。我常常觀察他的行走,當他身體的重心落在肢體的腿上時,身體內部彷彿會竄起一股扭動的力,促使他往前邁進,這股力不但形成了他作品中獨特的平衡感,也形成作品中筋絡糾結的木雕肌理。其次是作品的氣質,黃明鍾的作品無論是早期激亢的掙扎還是近期的安靜、恬淡,他的作品總是幽幽、委婉的流露著某種卑微。也許是藝術家人生歷練的影響,但也是眾生人性的共相。卑微,或多或少的普遍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內心幽暗的角落,沒有人願意彰顯而突顯自己的弱勢,在現代都市叢林法則下,藝術家總是過度自信且自負的看待這個世界,卑微早就被藝術家們超越、凌駕或是壓抑,反觀黃明鍾的作品,傾聽自己的內在,黃明鍾的質樸使他的創作更接近人性,也更接近自己。 黃明鍾的創作裏沒有深奧的藝術理念,也沒有花俏的形式語言,但正如本人一樣,土土的、鈍鈍的,卻有濃濃
[黎志文] 笑說他不去刻一些美麗感人的題材,卻專搞一些看不懂、怪異殘肢、格局生澀,甚至令人不舒服的作品。然而,當你耐心細看,你會發現作品內在充滿了生命的掙扎與無奈。他對藝術雕刻的追求,顯示出他對人生充滿的希望與自信的建立,是那樣的直接,從不矯揉造作,直接表達其內心的感受。
[黃祈文] 十多年來,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黃明鍾,堅定不移地走在這條創作的不歸路呢?或許是成長中不愉快的經驗,或許是不良於行所造成內外在的煎熬折騰,或許是屢遭白眼吃盡苦頭的學徒生涯…..,這些人生的歷練,更是他創作的原動力。朋友形容他,全身散發著表現主義,內在吶喊的氣質文脈獨自發展,木頭不語卻是至為貼心,他最怕在過多的欲求中信心不足而迷失自己,因此他不急於讓人歸類定位,在台灣當代木雕流域中御風破浪,他仍堅持走自己的路。 的人味。
五、未來期許
結婚數年(七月七日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我已不再是那個孤寂的黃明鍾,有妻一路挺我,有女以我為榮,未來的時間除創作外,更要花心思在她們身上,享受及體驗著家庭的愛及溫暖。當然,家庭生活對我創作有其必然性的衝擊,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自然,就讓我順其自然,讓生命在我的創作或生活裏自然展現其炫爛的光彩。

 商品類別
商品類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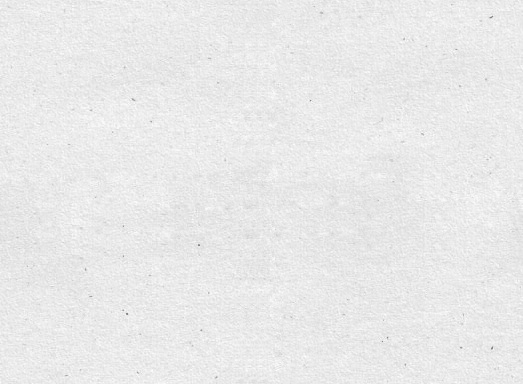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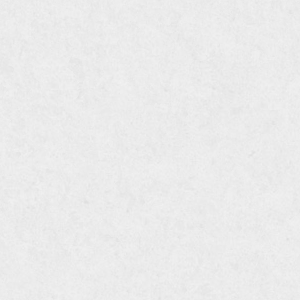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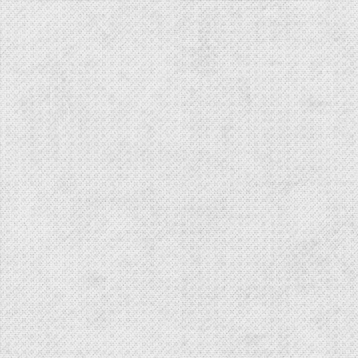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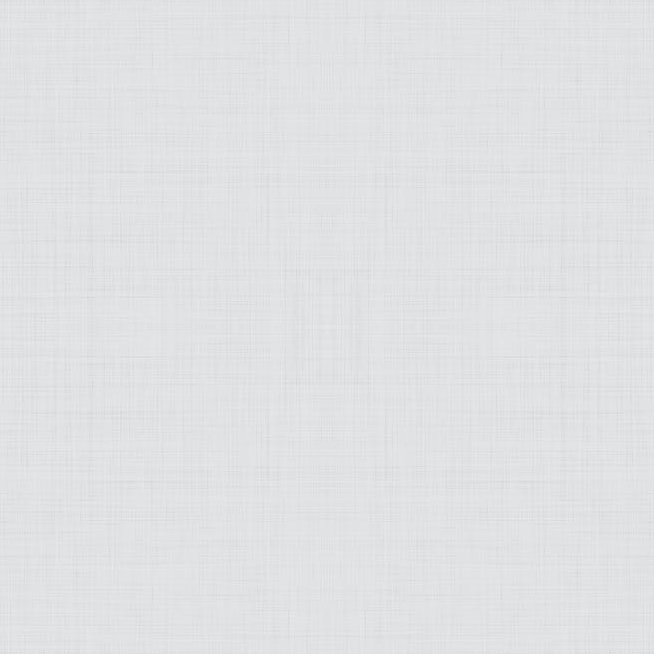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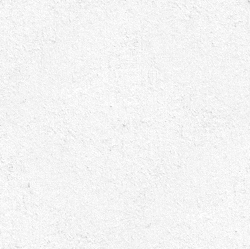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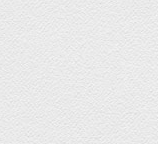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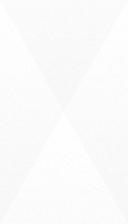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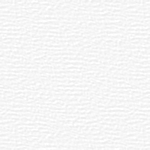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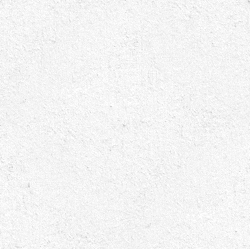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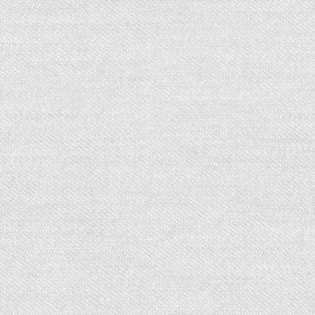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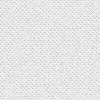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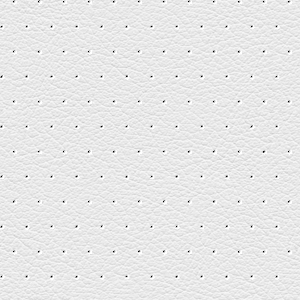
社群媒體